古代瘟疫的防治是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课题,早在《黄帝内经》中就有“五疫之至,皆相染易,无问大小,病状相似”的记载,历代医家在与瘟疫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,这些药材多依据“清热解毒”“芳香化湿”“补虚固表”等原则,结合瘟疫“湿热疫”“寒湿疫”等不同证型,形成了独特的用药体系,部分方剂至今仍对现代传染病防治有启示意义。

古代治疗瘟疫的常用药材及功效
古代瘟疫用药讲究辨证论治,针对瘟疫不同阶段的病机特点,选用不同性味的药材,以下按主要功效分类,介绍代表性药材及其古代应用:
清热解毒类:针对瘟疫热毒炽盛的核心病机
此类药材性多寒凉,能清解瘟疫中的火热毒邪,是治疗温热性瘟疫的主力。
- 金银花:性甘寒,归肺、心、胃经,具清热解毒、疏散风热之效,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其“治一切风湿气,及诸肿毒、痈疽、疥癣、杨梅诸恶疮”,古代常用于瘟疫初起发热、咽喉肿痛,如清代《温病条辨》中的“银翘散”以金银花为君药,配伍连翘、薄荷,治疗风热疫病。
- 连翘:性苦微寒,归肺、心、胆经,长于清热解毒、消肿散结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言其“主寒热鼠瘘,痈肿恶疮,瘿瘤,结热”,清代吴鞠通称其“能升能清,为治疫要药”,常与金银花配伍,增强清解热毒之力。
- 黄芩:性苦寒,归肺、胆、脾、大肠经,善清上焦实热、泻火解毒,张仲景《伤寒论》治疗“少阳病”(类似瘟疫中期)的“小柴胡汤”用黄芩清泻少阳邪热,后世医家多取其“清热燥湿、泻火解毒”之功,用于瘟疫高热、烦渴、苔黄腻。
- 黄连:性苦寒,归心、脾、胃、肝、胆经,为“清热燥湿、泻火解毒”之要药。《外台秘要》载“黄连解毒汤”治“一切热毒”,方中黄连配黄芩、黄柏、栀子,广泛用于瘟疫热毒炽盛导致的狂躁、发斑、吐衄,对细菌感染性疾病有抑制作用。
- 板蓝根:性苦寒,归心、胃经,具清热解毒、凉血利咽之效。《本草便读》称其“解热毒”,古代常用于“大头瘟”(类似现代的丹毒或病毒性感染),见头面红肿、咽喉肿痛者,如普济消毒饮中用板蓝根配黄芩、黄连,清热解毒、消肿散结。
芳香化湿类:针对瘟疫夹湿秽浊的特性
瘟疫常因“湿热疫”“秽浊疫”而起,湿邪黏滞易阻碍气机,需芳香药物化湿醒脾、辟秽和中。

- 藿香:性辛微温,归脾、胃、肺经,能芳香化湿、和中止呕。《本草图经》言其“治脾胃吐逆,为最要之药”,宋代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的“藿香正气散”以藿香为君,配紫苏、白芷,治疗瘟疫夹湿导致的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胸闷,至今仍是暑湿感冒、胃肠型流感的基础方。
- 佩兰:性辛平,归脾、胃、肺经,芳香化湿、醒脾开胃。《神农本草经》称“兰草”(佩兰)主“利水道,杀蛊毒,辟不祥”,古代用于瘟疫湿浊阻滞导致的脘痞纳呆、口中甜腻,常与藿香配伍,增强化湿辟秽之力。
- 苍术:性辛、苦,温,归脾、胃、肝经,燥湿健脾、祛风散寒。《本草纲目》言其“治湿痰留饮,或挟瘀血成窠囊”,李东垣在“升阳益胃汤”中用苍术配伍黄芪、人参,治疗瘟疫后期脾胃虚弱、湿浊内生,既能燥湿,又能扶正。
补虚固表类:针对瘟疫后期或体虚者的扶正祛邪
瘟疫后期或素体虚弱者,易出现气阴两伤、正虚邪恋,需补虚药物固护正气,助邪外出。
- 黄芪:性甘微温,归脾、肺经,能补气固表、托毒生肌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言其“主痈疽,久败疮,排脓止痛”,张仲景“玉屏风散”用黄芪配白术、防风,治疗瘟疫后气虚自汗、易感外邪,现代研究证实黄芪可增强免疫功能,抗病毒、抗感染。
- 人参:性甘微苦微温,归脾、肺、心经,大补元气、复脉固脱。《本草纲目》称其“治男妇一切虚证”,古代用于瘟疫重症元气虚脱,如《伤寒论》“独参汤”救急,现代仍用于感染性休克的辅助治疗,能提升血压、增强机体抗病能力。
- 甘草:性甘平,归心、肺、脾、胃经,补脾益气、清热解毒、调和诸药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言其“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,坚筋骨,长肌肉”,张仲景方剂中多配伍甘草,既能缓和峻烈药性,又能补脾益胃,顾护正气,避免苦寒药物损伤脾胃。
外用辟秽类:针对瘟疫的预防与环境消毒
古代还常用芳香或杀虫药物外用,以“辟秽浊、防传染”,如焚烧、熏蒸等。
- 雄黄:性辛温,归肝、大肠经,具解毒杀虫、燥湿祛痰之效。《肘后备急方》载“雄黄熏法”:“疫病流行,取雄黄末,水调涂鼻孔中,或烧熏居处”,认为其能“辟邪毒”,现代研究证实雄黄对部分细菌、病毒有抑制作用,但因含砷,现已少用内服。
- 艾叶:性辛、苦,温,归肝、脾、肾经,温经止血、散寒止痛、除湿止痒。《本草纲目》言其“灸火,通经活络,祛阴寒”,古代瘟疫流行时,常焚烧艾叶熏蒸居室,认为其能“避疫气”,现代研究证实艾叶挥发油对流感病毒、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抑制作用。
古代瘟疫常用药材简表
| 药材名称 | 性味归经 | 主要功效 | 古代典籍与应用举例 |
|---|---|---|---|
| 金银花 | 甘寒,肺、心、胃 | 清热解毒,疏散风热 | 《本草纲目》治一切肿毒;《温病条辨》银翘散 |
| 连翘 | 苦微寒,肺、心、胆 | 清热解毒,消肿散结 | 《神农本草经》主寒热鼠瘘;《温病条辨》银翘散 |
| 黄芩 | 苦寒,肺、胆、脾 | 清热燥湿,泻火解毒 | 《伤寒论》小柴胡汤治少阳病 |
| 藿香 | 辛微温,脾、胃、肺 | 芳香化湿,和中止呕 | 《局方》藿香正气散治湿浊中阻 |
| 黄芪 | 甘微温,脾、肺 | 补气固表,托毒生肌 | 《神农本草经》主痈疽;《金匮要略》玉屏风散 |
相关问答FAQs
Q1:古代治疗瘟疫的药材是否都安全有效?为什么?
A:古代瘟疫药材需辩证看待,部分药材如金银花、连翘、黄芩等,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其含绿原酸、连翘苷等成分,具有抗病毒、抗炎、调节免疫作用,至今仍有效;但部分药材如雄黄、朱砂等含重金属,长期或过量使用易导致中毒,现代临床已少用或禁用,古代用药强调“辨证论治”,同一药材对不同证型瘟疫效果差异大,且受限于古代制药条件(如煎煮方法、炮制工艺),其有效成分利用率与现代制剂不同,故不能简单套用古代方剂,需在医生指导下结合现代医学规范使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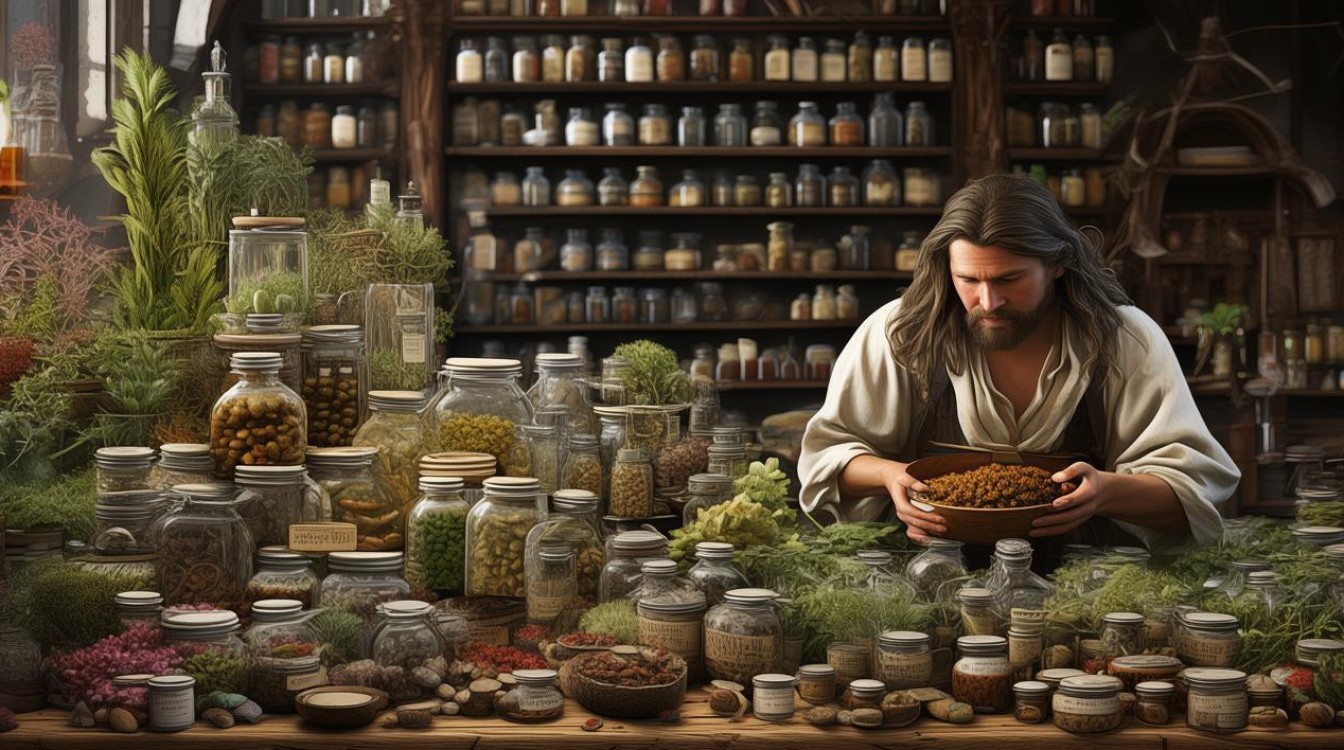
Q2:为什么古代瘟疫防治中常用芳香类药物(如藿香、佩兰)?
A:古代医家观察到瘟疫常夹“秽浊之气”,认为湿浊、秽邪是瘟疫传播的重要媒介,易阻滞气机、困遏脾胃,芳香类药物性味辛散,其挥发成分能化湿醒脾、辟秽和中,一方面通过芳香之气“开泄透达”,使湿浊从表而解;另一方面能调节脾胃功能,改善瘟疫常见的恶心、腹胀、食欲不振等症状,现代研究也发现,藿香、佩兰等含挥发油(如广藿香醇、佩兰烯),对大肠杆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抑制作用,还能刺激呼吸道黏膜,增强局部免疫,起到“预防感染、缓解症状”的作用,故成为古代瘟疫防治的重要药物。




